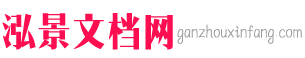散文:进不得村的船
去年的初夏我在伍家岗江边遛娃,看着从艾家镇过来的轮渡船靠岸,心里就想着等天气再暖和些我就带着我的孙女啵娃儿坐着轮渡船去对面的艾家镇去溜溜。
没想到这个想法没有机会实现,宜昌城区最后的一道过江轮渡线在盛夏的时候取消了。
想去点军想去江南尽可以选择公交线路,宜昌大桥,夷陵大桥,庙嘴大桥,还有在建的伍家岗大桥预计在2020通车。
其实我并不是想去江南,我只是想找一找坐在船上的感觉。船对江南人有抹不掉的记忆,而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条船我从没有看见过。
1973年初夏,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我和翠翠走上塘上小学后面的山坡,麦杆拥挤地顶着青晖,麦芒齐射象穿插在蕙子上的针。我们不走小道,撑开双手象展翅飞翔的蝴蝶让麦浪从我们的手下轻抚而过。麦慧饱满的青晖,让我想到了收割的快乐:“快要有锅烙子(1)吃了”我兴奋地说。
翠翠且有些自豪地告诉我:“我们队里造了一条船了。”她停下脚步,对着面前的麦浪双手比划着,像在飞翔又像在劈波斩浪:“我爸爸说那条船有我们家的道场大”(2)。翠翠的爸爸是队长,她家道场有十多米长,有三四条条凳宽,全是黄古石,即平又光亮,我们常去她家门前跳绳踢毽抓特务牵羊儿。“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它在河里,你看,”我们又跑到狮子包上,翠翠用手指东边的卷桥河:“我爸爸说等夏天水起来了,船就可以进到八队的河嘴上来了。“我说:”船能带我们去城里吗?“
“不行,”翠翠很坚定地说:”我爸说是搞运输的,公家的船小孩不许上。“我们的小队有一半窝在山里,每天上学都是上山,回家就是下山。山不大且很陡,直到现在做梦都有几坎上不去,回家且很顺溜,小跑着下山好像几十秒就到了家。我们的小队还有一半在山外,那里叫杨家湾,杨家湾隔着一条打铃岗,那里的一片农田都在岩上,岩下的小河叫长岭河,这条河还弯弯地走一公里就在八队的河滩边与车溪河(桥边河)汇合成卷桥河。
那次回家吃饭,妈妈也刚从杨家湾放工回来,捡了半篓子土豆用脚踩几下又用手提着篓子抖几下再踩,直到土豆一个个都脱了皮才让我拿到门前水沟里去清洗。
篓子一沉下水去,土豆皮翻起来,随着流水而去,我忽然想到了船:“妈,什么时候带我去坐船吧,我们队里不是有船了妈?”
在一边洗衣服的妈妈说:“我们队里的船小孩不能坐,是装东西用的,大人才能去。”
中饭,我吃着炕土豆问哥哥:”小哥,我们队里有船了哦!”
“我知道,王幺爹是驾长”王幺爹长得高大而且俊美,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电影演员王心刚。他的头发还微微卷曲,能拉二胡,夏天的夜晚它的二胡咿呀咿呀的,常把我们几个孩子听睡在星光下,直到爸妈把我们抱回房间里去,耳边还有二胡在轻吟。
不知过了多久,麦子割了,苞谷苗才尺来深,放学后的阳光睴煜,山道泛白,路边蒸腾的热气打着我们的小腿,当我们紧走到在山岗上,准备要往山下冲时,忽然一阵哭闹之声从山下传来。我和小翠站稳了脚步,仔细听时,那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小翠指着对面山脚下说:“你看,王大爷家门前好多人。”说完,她一下窜到我前面,飞一般跑下山去。
下午她告诉我:“我们队里的船翻在长江里了,淹死了八队的五个人,王幺爹也找不到了。”
从那以后,王大爷家不时就有人来哭。多少年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和王大哥同年的我的大哥就会说:“王幺爹怎么会死,他可以横渡长江,他是不敢回来。”这时候有老人就反驳我大哥:“大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王大爷倆老于八十年代初先后去世,王大爷家的房子被王大爹卖给了邻居,搬去了他乡。
我们队从那以后就租船用,后来修了双十路,我们队去宜昌城不是一担粪桶就是一担箩筐走到孝子岩去坐轮渡船过江。 卷桥河就在双十路下,安静在吐翠里,温暖在阳光里。
推荐访问: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