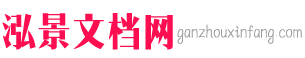散文:童年忆趣
生在水之湄,于是就和鱼呀、鳖呀结缘。鳖是我童年记忆中斑斓的一页。
我的故乡濒临赤湖,是个被冠以“鱼米之乡”称谓的滨湖小镇。每年三四月间,鱼类挺摆甩子的时候,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便挎个鱼笼去“捡”鱼,捎带亦捉龟鳖。
随便捉上一只龟,翻转过来,在格状龟板上用小刀刻上自己的名字,心里暗作“与龟同寿”的祈祷,双手捧着,送进盈盈浅水,令其慢悠悠划入茵茵绿萍之中。 有一次,捉来一只龟,在它的壳上竟发现了十多个名字,便多少有些嫉妒别人捷足先登,对这类“老龟”亦就敬而远之,任其慢条斯理去摆“老夫子”之派头。对张牙舞爪的鳖,我的乡亲们要“残忍”得多。在他们眼里,鳖亦同于其它鱼种,上天造出他们,就是送人类作下饭菜的。况且,鳖生性易燥,捕杀弱小鱼类,一张能断玉毁金的铁嘴,就连万物之灵的人类亦敢咬上一口。若被它咬住了,任你痛得呼天喊地,它也决不动一丝恻隐之心。鳖是水族中的凶杀恶魔。乡亲们便有噬其骨喝其汤的冲动,而其汤鲜味美,确有“绕口三日依回味”之效果。 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对鳖有种心理上的憎恶和生理上的偏宠。鳖,又称甲鱼、团鱼,俗称王八。我们那一带,通称脚鱼。下水游泳,踩着一块扁扁的“软石”,弯腰伸手,很谨慎地选择肚皮上四个微凹的肉洞,用手指牢牢扣着,提出水面,绝对是一只盛气的大鳖。鳖是不甘心就是这么被俘的,富有弹性的长颈挺着一颗椭圆形脑袋,从背上绕过来,呲牙咧嘴,两只小眼,射出幽幽的凶光。 捕鳖的最佳季节,是冬季和夏季。 朔风吹过,湖水赶趟儿被风刮跑了,露出浅浅的软沙。鳖就藏在这柔软的沙被下,诡秘地探出尖细的鼻子,悄悄地呼吸空气。人们只需把眼睛盯着平整的沙面,就能发现鳖的鼻子。
扒掉周围的沙子,鳖就在沙坑里很舒服地躺着,任你大声吆喝,它依然一动不动地继续做它的美梦。到了夏季,满世界被烤得热烘烘的,鳖在水里也闷得难受,常常在夜晚爬上岸歇凉。这时候,只需打着电筒,沿着湖堤“扫荡”过去,鳖凉爽得正惬意,你把它抓在手里它都懒得动一下,绝对不必担心他逃跑。就像拣石头似的,俯拾即是。 许多年过去了,故乡的鳖渐渐稀少,就连吃不得的龟亦难得在田沟里见到了。只有在市场上的“龟鳖部落”,才能一睹它们的“风采”,但没有童年的那份趣味。 捉鳖的趣事渐行渐远,只在记忆中温习。但虽隔着40多年的烟云,但那些细节、那些场景还是鲜活在我脑海中,让我每每口舌生津…… 露天电影的窖藏 最使我难忘的是孩提时在村野里看电影的情景。 黄昏的稻草上,竖起两根杆子,一块电影幕布,四个角被固定在两边的杆子上,喇叭箱像蝉似的爬在竿上,一张桌子,一台放映机,一个放映员外加一个徒弟,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拉着一个发黄的电灯泡,一个露天电影院就“建成”了。
露天电影没有严格的放映时间。天色咋咋黑,那个风景就呼之欲出:抽旱烟的、拄拐杖的、拖鼻涕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便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稻场上粉墨登场。此时,观众里,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爬到了树上,“风景”独特。我记得,每每有露天电影,最高兴的莫过于青春激荡的妹子和后生,最开心的莫过于“小箩卜头”们。那一晚,妹子们穿最漂亮的衣服,人显得格外的亮丽,后生们总是要到代销店拿一盒“飞马”、“壮丽”等上好的香烟和妹子们喜欢吃的瓜子、五香豆之类,显得无谓而兴奋。而那些“调皮”的小孩子们,看会儿电影,就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拿捏着腔调模仿电影角色的文艺腔和革命口号高呼上几句台词,惹来一片欢笑。 那时的放映设备很差,电影刚放一会儿或放到中间会突然坏掉,要么是没有图影,要么是图影上下跳动。
此时,放映师傅就重新倒带或检测放映机。年纪大的就会耐着性子慢慢等,年轻的、脾气暴躁的就会骂两句。小孩子们则趁机顺着光线表演一些手技,幕布上就会出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或者老头、老太太的样子,形态简单逼真,活灵活现。 多数时候,露天电影都能如期演完的,特别是秋天和冬天,天气比较稳定,只是春天和夏天老天常常“开玩笑”,有时摆好了架势正要开演,突然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落下,逼得大伙儿“落荒而逃”,嘴中骂骂咧咧地纷纷回到家中。 记得那时候,我经常会跑到幕布的另一面看电影。繁星下,夜风里,我一个人,扯来一把稻草或捡来一块小土块,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电影。《卖花姑娘》《列宁在十月》《智取威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那个时候,这些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 “高,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香烟洋火桂花糖”、“红军战士潘冬子”、“为了新中国,前进”、“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脸,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一个个难忘的片断,一句句经典的台词,像星光闪耀在我的记忆深处。 现在想起来,许多老片子的情节特别朴实,不像现在有的电影角色一句话没说完就开始拥抱、接吻。那时的影片,再亲切的战友见面也就是冲过去,紧紧地握手,然后上下摇晃几下,激动热情地说:“同志,可把你盼来了!”……这又使我想起当年在武大求学,第一次放寒假到舅舅家时,我舅舅竟然热情地跟我握手,我怀疑是不是他带我一起在他工作的矿山看露天电影时学到的。 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人儿趋之若鹜,呼这喊那,一片喧嚣。年轻人则多有初醒的美梦,满肚子的失落。胆大的后生则磨磨蹭蹭地找些理由边走边和妹子们闲扯刚放过的电影,融进些似曾相识的新观念,间或谈谈彼此之间的印象。
就这样,有露天电影作伴,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也构成了我对孩提时露天电影的怀想要素。是的,电影在村夜的篇章里确能添些淡淡相宜的插图。在寂寞的乡村里,在那个文化资源缺乏的年代,看露天电影着实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快事,也着实令人难忘、令人回味。的确,哪怕是再粗糙的生活,经由这些电影的滋润,同样也能长出希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