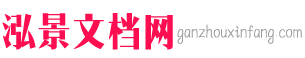农民父亲的“工人”生活
父亲是在县里一所有名的中学读过书的,当时村里只考上了两个学生,也算是个“秀才”,可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早早地“结束”了继续求学的岁月,回家当了一个农民。
父亲的兄弟姊妹多,他在家排行老大,三个弟弟妹妹还上小学,不巧爷爷又染上了结核病,需要长时间服药调养,家里的境况可以说相当的艰难。
刚刚下学,十七岁的父亲就被熟人介绍到了公社的沙场上班,因为没干过重活,铲沙、翻沙、拉沙弄得父亲瘦弱的身体伤痕累累,他有点儿吃不消,可沙场一月十二块钱的工资和六十个工分,让爷爷和奶奶不肯罢手。村小学的刘校长和村支部书记老马找了爷爷和父亲好几次,村子里缺老师,想让父亲去村里小学教书。可奶奶不同意,因为那时候做老师工资低,一个月只有四块钱和二十个工分,而一个农民,在地里劳动一天能挣到三分,此种情况下,爷爷奶奶当然看得见的只是眼前的日子,决不会因为当老师体面清闲或者说将来会有出息,而让他放弃沙场的工作。就这样,父亲一干就是八年,八年里,我的叔叔姑姑都一个个蹦蹦跳跳地完成学业,有的甚至成了家立了业。
三十岁那年,父亲因为工作认真出色,做人诚实厚道,还能写会算,被镇选派到采石场当队长,这队长其实不算个什么“官”儿,可管着石场里四十多号人呢,从生产、财物、账目到吃喝拉撒,样样都得须他操心把持。八0年前后,全队人一月的工资就得发三千多块钱,父亲一回也没弄错过。就这一点,跟他干过活的老马叔每次见我就说,你爸是个好人呐,没沾过我们一分钱。
父亲去石场上班的第二年,我开始上小学,才对家里有了更多认知和关注。在我和妹妹模糊的记忆里,母亲常常唠叨,人家马二总往家里拿个火铲、通条什么的,郑三哥常给孩子带点好吃的回来。怎么也没见你往家里拿过一个草棒儿。说轻了父亲不理,说重了,父亲也不急,他一边慢吞吞吃饭一边说,我是队长,不能跟他们一样,公家的,分毫我都不能拿,要这样,我还有理由管谁去!
娘也只是跟他怄怄气,是嫌他光干工作不顾家,有时月底工资发晚了,工友们都会一哄儿跑到我们家来领工资,母亲还得打酒做菜,忙个整晚是常有的事。
石场的车、锤、钎、叉、电线、电器、劳保护品很多,父亲从来没往家拿过一个铜丝儿,记得那年我们村里扯电灯,马二偷拿了十米电线回家,最终还是被父亲给要了回去,气得马二好长时间不跟他搭话儿。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迁到了邻村的学校去上学,冬寒路远,我的手常常冻破。母亲就说,你们那里劳保那么多,拿双手套来给孩子,谁知道?父亲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第二天下班,他给我带来了一双磨了两三个窟窿的旧手套,跟母亲说,这是谁扔在工地上不要的,被我洗干净了,你晚上补一补,给孩子先戴着,等下月发了新的,我再给他换回来。母亲尽管不高兴,还是熬夜补好。我嫌破,宁肯冻着也不愿戴,因为这,父亲又挨了母亲好几次“嘟囔”。
父亲没食言,发新手套的当天,他就把新的拿回来给了我,而那双旧的,被母亲补了又补,父亲戴了整整一个月。
我记得一年冬天,母亲到公路旁出义务工,扭伤了脚踝,肿得厉害下不了地,我和妹妹只能喝白开水泡玉米煎饼,看我们娘仨儿可怜,负责伙食的郑三大爷偷偷从厂里带回来三把油炸馓子,趁父亲没回来就送到了我们家里。父亲回来大发雷霆,那个月,他不仅扣了自己六毛钱,还扣了郑三大爷两毛,并对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弄得郑三大爷很没面子,在家里休了两天病假,父亲无奈,带瓶酒上门道歉,两个人喝得泪眼婆娑。
父亲也不是一件东西没往家拿过,他拿得最多就是那时的枣庄日报,日报每周一期的文学副刊,是我最喜欢的栏目,那里面的小说、故事、散文、诗歌让我回味无穷醉在其中,那时没有人喜欢看报纸,报纸不是拿去擦屁股,就是拿回家糊窗户贴墙,父亲见我喜欢这些东西,心里特别高兴,每个周末都会跑石场总部一趟,找一张副刊回来,这是他多少年也没有改变的习惯。
后来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国家基层工作人员,父亲也从社办企业下岗成了一个农民,可他常说的两句话却让我牢牢记在心里:公平公正才能做事服众,不贪不占才能做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