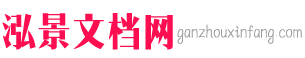散文 | 孙殿镔 : 一棵差点儿成了花的草
清明时节,一天早上,小雨淅淅沥沥,我来到自家菜地前。
说是菜地,其实小得可怜,夹在相对的两排车位之间,没有我一步宽,不足两个车位长。不过,蜗居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这已经足够金贵了。
去年栽的香椿已经长出四五片的茎叶,红色的,据说更好吃,可惜大点的只有一两片;前两天移栽的三棵金贞花已经完全恢复生机,此时更显得生机勃勃;西边的一些种子已经发芽,冒出小苗,我却忘记是什么种子,小苗也不认得,只能等它们长大揭晓答案了;其余的种子看不到动静,野草倒是撒着欢儿长。
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让我将“魔爪”伸向了野草。
野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野牵牛,大多长在东边埂上,大模大样登堂入室的很少,很快解决了。扯着它们与土地分离时,脑海里浮现出一朵朵红白色的喇叭花,轻微的断裂声只引起我微微的不安,毕竟只有两三棵。
另一种不知道名字,与河湖里的水白菜相似,深绿色,叶子好像放大了的柳叶,叶面上有两三条长纹,大一点的在四五片叶子中间还抽出一根穗子来,穗头是佛祖发型的拉长微缩版。它们放肆得多,不仅仅边埂上,菜地中间也已安营扎寨。我如法炮制, 嘣嘣蹦,一声声低沉的断裂声传来,我越发不安,仿佛自己正在疯狂杀戮。
“喂,住手!”当我再次伸出手时,手下那棵野草竟然扭动着身子,发出声音。
“哦?哦!”我的惊讶可想而知。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它悲愤地责问。
“嗯,我这是菜地,你们都是野草,妨碍菜蔬生长啊!”
“野草?谁告诉你的?”
“哦,大人吧!”
“那谁告诉大人的?”
“大人小时候,他们的大人告诉他们的吧。”我有点狼狈,只好胡乱猜测。
“哼!真可笑!真荒谬!”野草一脸不屑,“你们人类将我们植物分为农作物和野草,你们还将动物昆虫分为害虫和益虫,你们划分标准是什么呢?”
“哦,大概是看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吧。”
“答对了!你觉得这样的标准自私吗?要是我们植物动物来分类的话,你们人类保准是最大的野草、最坏的害虫,这是毫无疑义、千真万确、众望所归的!”
这棵野草竟然也爱拽文,还不伦不类地叠床架屋。不过,它的话倒是有几分道理,我思考着,一时怔在那里。
“好啦,好啦!别想那么多啦。”它有点不耐烦,脸色一正,继续追问,“你打算怎么对待我?”
“这,这,当然也是拔掉丢弃啦!”
“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样?”它语气缓和下来,甚至有点讨好的意味,“你别弄死我了,我也不在这里妨碍你的菜蔬了。你爱养花,你将我挪到家里的花盆里,当花养怎么样?”说到这里,它已是一脸媚笑。
“你怎么知道我爱养花?”我疑惑地看着它,它是附着了神意的精灵吗?
“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凡像你们这样在蜗牛角里做道场也要栽种点儿菜蔬的人,有几个不喜欢养花?”
也对,我的智商竟然不如一颗野草!
“可你也不是花啊?”我故意皱着眉,一脸的深沉。
“哼,你家的那些花是怎么来的?它们也不是农作物或菜蔬吧!其实,我们大家都起源于同一家族,那就是野草家族,说起来,还是我们基因强大,既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家族的特质,又繁衍绵延至今。其实,整个地球上,我们的数量远远大于被你们人类驯化的树木作物花草。也就是说,你家里的花草都是变异的野草,我们野草是纯种的花草,这句话您听得懂吗?”
我似懂非懂。它不知不觉间用上了敬辞,求生的力量真是强大,被尊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不禁嘴角上翘。
它仿佛受到鼓舞:“好了,您不必考虑这些了。您爱读书写东西,知识渊博,想必知道那句名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您看看,我的身姿其实挺不错的,栽到花盆里一定更漂亮!”
我看着雨中起舞的它,脑补上花盆,别说,还真不错。
“再说,想想您自己,不也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一棵野草吗?只不过现在是一盆花了。对土地、河流、村庄、庄稼、畜禽等,您现在不还是充满了天然的亲近感吗?您小时候也是在土窝里打滚,在田地里疯跑,在池塘里撒尿,在园子里偷苹果、偷梨子、偷西瓜、偷·······”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我赶紧打断它,一迭声地应允着。我擦拭着鬓角上的水——雨水和汗水混合成的水,有点敬畏地看着眼前这棵野草,它大约真的是通神性呢。
我将它轻轻从土里拔出来,在旁边的雨水洼里涮了涮。
“哦,不要,带点老土,我更容易适应花盆里的生活。”它抗议道。
“哦,那不行,首先,作为人类,我不能弄脏自己的手;其次,作为盆花,你不能脏兮兮的。否则,被我家里的河东狮看见了,她会一把夺过去丢到窗外的。”
它乖乖地闭上嘴巴,闭目忍受着雨水的洗刷,根须很快变得白生生的了。
我拿起它,转身往家走去。
“喂喂喂,还有我们呢?”一片喧哗声起,扭头一看,那些刚被拔下来的、那些还没拔下来的野草一齐向我招手,“再带上我们吧,我们也是美丽的花呀!”
我大惊失色,丢了手里的那棵野草,落荒而逃,顾不上脚下水花四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