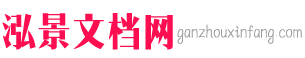梦回庐山(庐山情书)
我和庐山的第一次相见还是在我读大一的时候。那时我在南昌大学读书,身在赣州的小表弟江江思念他远在庐山工作的父亲,于是我便带着“使命”,领着小表弟上山看望他父亲。
记得那是春天的傍晚,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不断地向山顶盘旋。天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浓的云雾遮住了山路,四周白茫茫又暗沉沉的一片,我们感觉离人类文明越来越远,似乎将迷失在这虚无缥缈的云雾中。10岁的表弟患有中耳炎,又晕车,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低压感让他痛苦难耐,他捂着耳朵沮丧道:“哥,我爸真的在山上工作吗?他会不会变野人?”
我搂着可怜兮兮的弟弟,心疼得不得了,于是点点头:“会!”
弟弟面如土色,紧紧抱住我的腰,被汽车甩来甩去,他带着哭腔像和尚念经一般数到:“216个弯,跃上葱茏四百旋,217个弯,跃上葱茏四百旋,218个弯……”我感到欣慰,教会了他不少知识。
量变引起质变,不会晕车的我,经过几百个急转弯之后,也晕了。弟弟吐了两次后开始不数了。我有些怀疑毛爷爷当年上山时是不是火柴不够,数错了数,上庐山根本不止400个弯道吧!我佝着翻江倒海的肚子,想起爸爸教我的晕车时就看远处,但眼前皆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没有什么远处可言。
“哥,到了山上,我们怎么找爸爸?云雾这么大,看不见他。”
“靠气味!”我苦中作乐,逗他,“你一定能分辨他的气味!”
“哥,我开始眼花了,”弟弟揉了揉眼睛,“雾怎么都是金色的?”
又是几个大弯道,我们冲出了这层浓重的金雾,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金光灿灿的,全新的金色世界!这时,雾是金色、云是金色、峡谷是金色、树木是金色、路也是金色,我望着金光灿灿的弟弟,指着两山拱托的一颗大金珠,喊道:“弟弟,快看,是日落!”
“太好啦,太阳下山了,”弟弟爬过我身边,扒着车窗,兴奋道,“我可以和爸爸一起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啦!”接着,他又失落道,“可是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有电视看吗?”
弟弟就知道看动画片,根本没有体会到日落的真正含义,于是我纠正他:“日落,意味着人们一天辛劳的结束,意味着待会,我们可以吃晚饭了。”我望着日落的尽头咽了咽口水。那种“又晕又饿”的感觉,恐怕是只有上过庐山的人才能体会。
美丽的日落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动画片和吃晚饭的诱惑使我们重新打起了精神,我们剩下的担忧是: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有没有电视,和好吃的……
汽车开始驶入下坡的弯道,我推断,山顶快到了。
驶下坡道,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阵夹带着云雾的凉风,映入眼帘的是一池碧绿的湖水,四周环绕着青松翠柏,湖面上“飘”着一座孤傲的八角亭,与前方一座犹如“白龙饮泉”的拱桥隔水呼应。
“叔叔,停车,快停车!”弟弟突然大喊。
对!快停车,太美了,这是我梦中的仙湖。
车“嘠”地停住了,我打开车门,对着芦林湖不禁吟诵道:“叠叠苍峦别是天,往来即是地行仙。拨云峰底落红雨,冷翠谷中浮紫烟。”
“哇——”弟弟猛地推开我,如此仙境,他居然又吐了!
稍作片刻逗留,弟弟恢复了精神,我们继续往前行驶,上坡。我们开始看见了很多“红顶石屋”,就像老上海电影里的小别墅。弟弟终于露出了断了半截的大板牙:“哥,山上的房子不是茅草屋,我爸不会变野人!”
我告诉弟弟,不一定。
我们路过了用花岗岩搭建的教堂,又看见了用花岗岩搭建的电影院,便讨论着电影院里会不会播放《宝莲灯》。开车的叔叔告诉我们,那里全年只循环放一部叫《庐山恋》的爱情电影,还说有亲嘴的镜头,我很想看,但未成年的弟弟不能看(脚注1)。接着,我们穿过了一条犹如(曾是)防空洞的隧道,终于来到了牯岭街。
那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世外桃源”。在苍茫隐秘的山巅上,居然藏着一座繁华的城市,而在那条贯通整个景区的“云上天街”——牯岭街上,华灯璀璨、游人如织。透过如梦如幻的七彩云雾,我们隐约看见了:餐馆、面包房、商场、咖啡屋、书店……司机叔叔还告诉我们,早在30年代,庐山就有这些商店。太神奇了!这座城市在我爷爷都还未出生的年代就已经如此繁华,这简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山上到处是霓虹闪烁的饭店和旅馆。没有了吃住的后顾之忧,弟弟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他“未变成野人”的爸爸,我们也有了生活保障。之后的几天,我们便开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庐山之旅。
层云浓雾、山高路盘、天空之城、绿水青峦,便是当年无忧无虑的我对庐山的第一印象。从此以后,我便时常教育弟弟要有孝心,他爸爸工作辛苦,该常常去看望他,最要紧的是必须由我带他上山。于是,大学几年间,我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庐山之行……由南北门乘大巴或从好汉坡步行上山,看“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各个节气的庐山。
我读大四的那年冬季,估约是第十几次上庐山吧。我和哥哥洛基凑份子,“强迫”弟弟上山去看望他爸爸,我们也顺便看看雪景(确实是顺便)。哥哥那次带了个美女一起上庐山,现场表演了“庐山恋”给我们看。好在那个美女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嫂子,要不然,这一段也是不能写的。在这里,我顺便对嫂子说一句:“嫂子请放心,哥哥只谈过一个女朋友,那就是你。当然,信不信由你,打轻一点……”
言归正传,我们四人雇了一台面包车,准备从北门上山。司机在北门口抽出四条胳膊粗的铁链,甩了甩。13岁的弟弟很害怕啦,他的安全意识比我们都强,拉着我们三人围作一团,打着商量:“哥,四条铁链,我们四人,刚刚好!”
我和洛基脑子转不过弯,嫂子也不明就里,于是便问他什么意思。
“一人一条,绑我们,拐卖我们!”弟弟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满头大汗。
我们三个成年人,瞄了一眼比弟弟还瘦小的司机,又看了看未成年的弟弟,满脸惊恐道:“完了,完了……这该如何是好呦?!”
弟弟用“蚕宝宝”似的的小手,指着园门内一条犹如白蟒爬坡的山路,奶声奶气道:“我们快跑,跑上山,找小头爸爸……”
“你们上车吧,车轮的铁链锁好了,”司机指了指五花大绑的车胎,“这样就不会打滑啦。”
我和哥哥嫂子捧腹大笑,架起弟弟上车。弟弟像“猪崽子”似地挣扎着,双腿在空中蹬腾,杀猪般尖叫道:“阴谋,帮凶!”
北门的山路相对南门平坦,路面上结着新鲜的冰渣,两侧堆积着清扫后的冰堆,带铁链的车轮稳稳当当地碾压在冰面上噼里啪啦作响。道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的枝干上没有了树叶,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细长的冰凌。迎着车窗而来的,云非云、雾非雾,像是一颗颗细小的冰沙,夹杂着轻柔的雪绒花……
“小伙子们,庐山的冬天美不美?”司机小哥问道。
“美,美极了!”我们答道。
“大多数游客,只知道夏天来庐山避暑、秋天赏枫叶,却不知道庐山的‘春之盎然,冬之磅礴’。”
“磅礴?冬天都是凄美的,怎么是磅礴的呢?”我不解道。
“待会我们会路过望江亭,你就知道了。”
我们沿着这条“白色巨蟒”,路过了小天池,看见了比以往更加圣洁的“诺那塔”。塔周往日的青松翠柏,今日变成了绵亘不断的洁白的哈达。车继续前行,我们看见了山下的世界,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白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是城市还是村庄,房屋或是桥梁。
司机在望江亭路边停下了车,小憩片刻,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去亭边看看什么是庐山冬天的“磅礴”。我们牵着弟弟沿着冰雪覆盖的石道往望江亭走,穿过刻着“山河不二”的花岗岩碑门,蹬上悼念九十九路军的九级台阶,来到了冰雪覆盖的抗战烈士陵园。抗战纪念碑在风雪中矗立着,碑顶像把尖刀直插云霄,象征“三民主义”的三角锥形的碑身,迎风面盖着一层圣洁的冰雪,背风面横挂着一串冰凌,像烈属们的泪。我们在抗战纪念碑前默哀……
抗战纪念碑后面的一条羊肠小道通往“烈英亭”,即77年后改名的“望江亭”。我们钻入白松掩盖的小道,迎着刮皮刺骨的寒风,登上了望江亭。庐山整个西北面尽收眼底,左右两座山峰掩映着九江城,阵阵冰雾扑面而来,这里是圣洁的世界,这里是冰雪的王国。冬季的庐山确有磅礴壮美之势,我不禁吟诵毛爷爷的《沁园春·雪》,哥哥、嫂子、弟弟跟诵:“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那一次,我们体会了程公许的“未暇双林寻净侣,试招五老对苍颜”,王世懋的“千崖冰玉里,何处着匡君”,徐凝的“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陆游的“烟霞华岳逃名客,风雪庐山入定僧”和“泥巷有人寻杜甫,学庐无人问袁安”……
那一年我和哥哥洛基即将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在庐山上我们对着大雪磅礴的庐山,雾蒙蒙白茫茫犹如我们未来的世界,踌躇满志,又有些失落彷徨。哥哥说:“春夏秋冬、黑夜白昼各有其美。人生不可能处处是鸟语花香,严冬黑夜来临时,我们像冬登庐山一样依旧小心翼翼又豪迈前行,美景便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眼前!”
岁月如庐山的云雾,悠悠而过,漫延不绝。转眼间,童年远去,我已创业十年,已有了小儿恩恩和贤妻钰杰。我生性“贪婪”,现实和梦想都不曾放弃,终日在工作、生活、音乐、写作中反复切换。电话日夜轰炸,琐事闲客不断纠缠,最令我嗟叹人生悲哀的是,身边一些至亲至爱之人开始逐一离开了我:曾祖母、爷爷、奶奶、外公、满公(脚注2)、大姑、小姑、尧九、阿飞……这些亲友们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永远永远地失去了他们。
我嗟叹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渺小。于是,疲惫时的我,开始习惯了种种追忆,追忆庐山上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追忆叠加到一定程度,便影响了我的行为,我决定再上庐山。
那一年是秋末,估约是我第二十几次上庐山。我在九江和客户签订了所谓的“大合同”后,让同事如期回赣,而我便把车停在山脚下,独自一人从好汉坡徒步登山。那次徒步好汉坡,离我第一次徒步好汉坡,已整整十五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呢?
长长的青石铺成长长的台阶,长长的台阶组成长长的好汉坡,这条长长的好汉坡即像我们长长的人生,充满坎坷、曲折,看似长长,当我们快要走完时,回头才发现,其实开头和结尾是否只是一瞬间,这一路的艰难和喜悦,是否只是我们自己的幻念。
枯枝败叶掩盖着青石台阶,光叉叉的树枝左右横生,我“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吟诵着曹操的《短歌行》,唤孟德作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三分天下的雄霸之主尚且如此呼!
阵阵乌鸦的哀鸣由远及近“哇呜——哇呜——”回荡着。
“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首诵罢,我差点把“哺”吐了出来,断了气。这几年被“猪朋狗友”搞坏了凡身肉体,体力不如当年啊。我这只乌鸦,是不是该找根树夸子“依一依”。
好汉亭,就这么善解人意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像狗刨土一样,手脚并用爬到好汉亭,哆哆嗦嗦地掏出“瑞香”,猛吸一口,撇见禁烟标示后,又吸了一口,反复掐灭。思绪随着烟雾,和乌鸦的“啊——啊——”声飘向远方:我这次是留半条命,做半条好汉,还是丢条命,做整条好汉?“蒋委员长”坐轿子上去,我走到一半,不算丢脸,再说,以前我也算走过……
半途而废不是我的风格,我像上了岸的水虿(脚注3)一样,爬上了好汉坡,来到了剪刀峡。我躺在冰冷陡峭的石阶上,指着“月明星稀”的夜空,放声大笑:“要阻挡我前进的脚步,没门!有本事,就多来几组台阶,你吓不倒我!”
确实,没门!剪刀峡的铁门到点就关了。我进不了园门,蹲坐在剪刀峡铁门外的石阶上,冻得瑟瑟发抖,涕泪直流。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四周乌漆墨黑的悬崖峭壁,吹着嗖嗖山风,莫名想起了景阳冈上的“吊额白睛虎”。尽管我知道“草木深茂,虎豹纵横”的庐山,是在1000多年前的明初,但在这种环境和心情下,想想也着实吓人。
实在没办法,为了不被冻死或被自己心里的老虎给吓死,我还是——报了警。门开了,我差点奔溃,我全然忘记了,剪刀峡到牯岭街,确实还有几组长长的台阶和陡坡……
那一次,我没有去寻访耳熟能详的景点,也没有去查究那些文人骚客们关于庐山的诗词歌赋以及成文背景。我一个人,信步由思,在不知名的小坡、山道、林径中穿行,寻找那些被人遗忘的风景,以及我内心里关于庐山的那种纯粹的快乐。弟弟、哥哥、朋友们,这次都不在身边,庐山还是这座山,我却不是原来的我。
我开始孤癖——喜爱孤独,我学会了与法国梧桐、日本柳杉、台湾云松、鹅掌楸、鱼腥草、小野菊……尺蠖、蜘蛛、椿象、寒蝉、蝴蝶……百灵、云雀、乌鸦、臭鸪、岩燕……乃至一石一墙、一屋一垣做朋友,我学会了与自然万物成为朋友。我与云雾、蓝天、明月星空为伴,我可召唤各朝各代的文人骚客为伴,我感到“无枝可依”又“枝枝皆可依”,我亦是乌雀可依的树枝,我感到无与伦比的解放。我的身心融入自然万物——我便是自然,我就是庐山
(如果每个人这一生去庐山的次数在“宇宙这本大账簿”中早有定数,那么,我每次去庐山,是多一次,少一次,还是不变的呢?这本大账簿,更改了吗?)又过多年,多年之中,我亦多次与亲友、客户浅游庐山,但每次下山回到千里之外的赣州,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心里感到空荡荡地并期盼着下次上庐山,把心中那块不知名的空荡区域,用某种回忆和感悟填充。那种期盼好似人生的长跑,脱水一样,跑得越远越想上山喝一口山泉,但那山泉的味儿比起初上庐山时,总是少些感觉。是少了什么感觉呢?
于是乎,我开始想庐山,梦庐山,解析内心深处关于庐山的那块空荡区域。时至今日,我坐在赣州“摘星楼”(脚注4),第一次提笔描山。在山上的日子,如此逍遥快活,以至于我不舍得花一秒钟做任何与游山悟道无关的事,我酝酿已久的,关于庐山的“情书”——情感之书,就在千里之外,用我的梦、回忆、神思、感悟来完成吧,或许此次“上山”,能填充我心中关于庐山的那块空荡荡的区域。
这估约是我第三十五次上庐山,我的本体在赣州,神、思、梦,穿越时间、空间、维度,飘往梦中的庐山——我梦回庐山!
这几日一直都是中秋佳节,小姑把爷爷奶奶接到南昌小住几天,我坐着107路公交车(脚注6)从学校出来,到八一公园陪爷爷奶奶散步。公园内张灯结彩,欢声笑语。爷爷丢掉了拐棍,打个背手,挽着矮矮胖胖的奶奶,指着湖面上的月饼灯对我说:“孙儿,明天我们去东林寺接你曾祖母(脚注5),你可别忘了叫你爸爸带她爱吃的果仁月饼哦。”
“你爸爸最疼他奶奶了,”奶奶抚摸着我的头,一脸慈祥,“子曦也要疼奶奶哦。”
我抱着爷爷奶奶亲昵,太开心了,明天就能接曾祖母一起上山,她在东林寺持戒礼佛,100来岁了呢。对,我还要把钰杰,恩仔一起叫过来,曾祖母和爷爷奶奶都没见过恩仔呢。
第二日秋高气爽,我们坐在107路公交上,沿着掩映着枫林的小道,开往东林寺接曾祖母。温煦的阳光穿过火红的枫叶撒在大巴上,我推开手动车窗让凉爽的山风灌满整个车厢。倒梳着一头银发的爷爷架起京胡,奶奶随即唱起了《梦回庐山》的京剧:“慈母沥血病床吟,张生寻药入庐林。救得白雀坠崖去,神女报恩化金灵……”(脚注7)车上欢声笑语,爸爸妈妈和姑姑们纷纷鼓掌喝彩,大姑小姑都在。恩恩拼着乐高,坐在钰杰怀里,摇着小脑袋哼唱着。表弟江江和表哥洛基在玩“任天堂”(脚注8)。
“子曦,东林寺到咯。”司机是尧九,他回过头来,笑容满面。
“大哥,我们一起去接妈妈吧。”满公醉醺醺地对爷爷说道。
爷爷硬朗地站了起来,牵着奶奶一声令下:“走,接妈妈,上庐山赏月!”
“哦,接奶奶咯!”“接曾祖母咯!”“接高祖母咯!”
爸爸妈妈、姑姑姑丈、兄弟姐妹、尧九赖飞、恩仔凯凯……欢呼雀跃,跟着爷爷奶奶下了车。
东林寺外松柏参天,遍地红枫,袅袅云烟从雕梁琉瓦的高墙内飘散出来。我们叩了叩铜环,推开朱漆木门。门“吱呀”一声打开,惊走了一群乌鸦。一位头戴黑绒额帽,身着湛青褂衣,脚穿黑裤黑布鞋的驼背老太太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正在用枯树皮似的手,为几盆盆景拆除捆绑的铁线(脚注9),口中念念有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妈——”“奶奶——”“曾祖母——”“高祖母——”我们喊着土白,冲上前,跪在她面前,扬起头端详着她。
曾祖母头顶着太阳,笑起一脸的皱纹,瘪动着嘴,露出几颗假牙,哆哆嗦嗦地从褂衣侧袋掏出红包,逐个派发:“美堂、秀珍、明古、伟香、子曦、钰杰……恩恩是我的玄孙吧?我还没见过哩,好好好,儿孙满堂,儿孙满堂……”
我们挽着曾祖母上了大巴,从南门往山顶方向开去。沿途没有了站在马路中间揽客的商贩和导游,也没有了像飞机一样过弯的本地汽车。我们在夕阳下、秋风里、山水间、白云上,欢声笑语,围着曾祖母,倾诉着近二十年的相思。
尧九开着车子绕到了望江亭看日落,绕到了含鄱口看日出,绕到了观云亭看云海,绕到了花径看百花,绕到了铁船峰看劲松,绕到了三叠泉看瀑布,绕到了锦绣谷看仙人洞,绕到了剪刀峡看断崖,绕到了谷云峰看江湖,绕到了大月湖看流星,绕到了庐琴湖听春雨,绕到了芦林湖看秋色,绕到了牯岭街看冬雪,绕到了大林路遮夏荫……
汽车就这样一路开着,开着,我们不会累,也不会困,周边的景色呈四季变幻着。大巴最终来到了香山路38号,我们的寓所“花园别墅酒店”,我们在花园里摆出糕点水果,摊开餐布,席地而坐。
曾祖母坐在藤椅上,透过园中的那两棵百年红豆杉,仰望星空道:“子曦,月亮可以出来了吧?”
“太太(脚注10),请您等等,我朋友们还没到齐。”我快速闭上眼睛苦思冥想,朋友们逐一出现。我抚摸着旁边的一株藤萝,又开了一瓶青岛啤酒,季羡林和丰子恺老先生也相继出现(脚注11)。
我望着所有的亲人和朋友,而后对着星空大喊:“月亮,你出来吧!”
来了,来了!月亮在空中隐现,黄黄的、白白的、胖胖的、圆圆的,它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嫦娥姊姊挥舞着“彩云纱衣”从月亮上飘下,落在花园中翩翩起舞,玉兔和我的宠物“咪咪”(脚注12)在曾祖母的藤椅下嬉戏,爷爷搂着奶奶在跳交谊舞,恩恩和凯哥在月影下躲猫猫,朋友们高谈阔论、吟诗作对,我纵情高歌并流连于亲友之间,斟酒倒茶,派发月饼……
这是最团圆的庐山之行,有最美的夜,最圆的月。我终于找到了庐山回忆中那块缺失的拼图,那便是所有美好回忆的叠加,是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永远永远无法再次拥有的幸福。我泪流满面,哭声把我从梦境中唤醒,我顾不得擦干泪痕,快速执笔记录下这一切,将我的幸福永远定格在这篇《梦回庐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