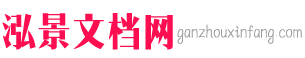侧耳倾听一片春
一场如约而至的太阳雨洒到大地,已明显润出春的印迹。土地弥漫出一股霉烂的潮气。光影把雨丝浥入枯萎的土地。门前这株老椿,虬枝低垂。显然不可抵御这“三水”相湿的邀约了。那萧条中已包裹着某处柔软,不再有固执的凛冽。
当一抹浅绿挂上了枝尖。微笑便吐出了一粒粒鹅黄蓓芽。晶莹莹。我相信这是心甘情愿的敞亮。因为等待有时是突兀的,悄无声息的。那渴望便是一阵雨过后的诧然了。这诧然,不是因为地上还有一点点稀疏的嫩草再频频抑视,或者还有满地的落叶败絮占领着大片领地。
那是嫣然与残败相映成趣,孱弱与霸道妙趣横生。这是什么样的景致?这样不可理喻?当柔韧以弯弯曲曲,柔柔长长伸向冬的深处。甚至以柔弱的姿态,谄媚尘世。那么苏醒复活便是一种必然了。那些在变硬的泥土里找到的归宿,那些放肆地踏踩过去的鞋跟,那些逃离地面的饥饿,那些拥有过最温暖的子宫。那些隐约抗拒的呓语。
轻松脱掉一件件厚实的冬衣,只是身体自愿靠近一种舒适。那些习惯于只与自身相处的眼睛。排斥接触,刻意的捍卫。就像挂上了虬枝上的嫩芽,在无比硬实之上建立的是还是无比的柔软。落叶败絮将在这场春雨中腐化成泥。世界并不忧伤。只是令人出神罢了。
出神这种相映成趣,这种妙趣横生。滋养和新生,厚积与薄发,索取与回馈,何时开始?周而复始的大地已经静悄悄的开始了春天。那是自愿靠近珍贵的沉醉和听语般在滴落的前奏。
一直不知道春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有如清晨睡眼惺忪的我,推窗罕见几只小绣眼在老枝翩然而蹈,啁啾呢喃。我又何尝会想起香椿煎鸡蛋的鲜香呢。我何尝看到过夜间安静山林间,正上演着一场万物复苏的音乐会。我却分明听到一颗颗春笋挣脱泥土束缚勃发出的“咔咔”声。生命韵律的声音其实是舒缓的。一切皆是在静默中开始,我还听到天际传来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舒缓是静默的节奏,弥散是心澄的旋律。季节的时钟缓缓摇摆,音符的弧线声如细丝地划出一道轻盈的天韵,响遍山林。凝神静听,我看到一双纤纤柔荑斜斜压过琴弦,天鹅绒温柔的触感在指板间灵容起舞,精灵般滑,揉,颤,跳,是那样柔韧缠绵。张弛间划出的韵律又是那么超然物外,质感饱满。没有一丝匠人手中藏不住的焦灼和稍纵即逝的浮光。这声音,有色彩,有温度,还吟唱着留得住的故事。是谁让音乐的句子这样富有青春生命?令我这个爱乐人妒忌得甚至想把自己一双僵硬拙手砍掉,别去糟蹋这份静谧的自信和乐观。侧耳倾听,婉转间,忽高忽低,忽明忽暗在慢慢靠近我,我听到寂静中一张张错落有致,反差极小的色平面。毫不费劲。晃晃悠悠,开始伸展开来。我恍然明白,春天女神才是位高超的演奏家,她正用女性特的一种宽容与信赖,拉响了一首春到人间草木知的夜曲。
倘若请你静卧林丛间,轻轻合上眼睛,听听这春夜的声音,柔和开始变低,低到极处,几个盘旋,又再低沉下去,那是银弦荡着几点疏星。月光洒上大地上。声音又瞬间跳起来。虽极低极细却不碎裂。那是苞蕾在绽放,新芽在破土,嫩枝在抽条。一阵弦音凌空而起,飘忽不定,夜风开始抚摸氤氲草坪,水面划过帆影,刹那之间,敲击与滑碎连成一条蜿蜒波折,轻摇的柳条突兀地跟着长长波折的掠过屋檐,穿透了苍穹,飘向大地,惊了一窝新垒的燕巢。
你也迎来了一种穿云裂石的惊悚,这惊悚,震颤却不嚣张,雏燕“唧唧咋咋”的声音紧围着潜移默化地回旋。你恍然发现,春天形成了,蓬勃了,蔓延开来了,步伐越来越有力,色调越来越明快了。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种种野花,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更多的生命从松软的泥壤中冉冉升起,姹紫嫣红在柔和的风里酥透欲滴。无论是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心里呼吸,痛饮甘露般陶醉、清洌。也许只需待到日出,翡翠的葡萄叶就会爬上那颗老藤茎。
仿佛一直以来就喜欢和安静相关的事物。月光,寺庙、夜雨,幽谷,无人的山林、深深的自我;沉沉地陷溺,永恒的爱恋......一直以来,我却偏执地理解了春,以为春只属于烟梦和繁华。在数不清的心理密码和笨拙动作中寻找。而今却发现,春更是阴柔恬静润湿的乐章。只要春和静这个字一沾边准会刹那间,侧耳倾听一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