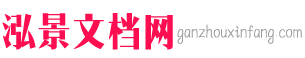放不下的惦记
冷峻先生在谈到什么是艺术时给我们讲了他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有一次我坐上去哈尔滨的列车,紧挨着我身边的乘客是个身着天蓝色汗褂的姑娘,那姑娘要身材有身材,论长相有长相,坦白地讲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最漂亮的女人,说她美如西施一点也不过份。爱美之心人人有之,车厢里那些不安份的男人们不时地将目光投注到这位貌美的姑娘身上,瞅得我坐在那里老觉得别扭。我并没有因为那些讨厌的目光而离开自己的座位,一反常态,能够和美女坐在一起反而觉得是一种荣幸,我巴不得美女永远坐在我的身边。
列车飞快地奔驰着。每停靠一个站台我都担心身边的这位美女突然下车离我而去,真的希望列车就这么无限制地开下去,我永远地坐在她的身边。自我的陶醉,你说我是自作多情也好,你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罢,不管怎么说都行——这就是我的一厢情愿。蠢蠢欲动的灵魂萌发着占有的欲望迅速地燃烧着。
列车到了吉林附近的一个小站,那位坐在我身边的漂亮姑娘突然下了车,我瞅着她消失的背影顿觉空茫,刹那间我好像失去了一个支撑的依靠,存放在心里那份美好一下子全部坍塌了。懵懵懂懂地心间就冒出了酸水。
那时,我才二十多岁,不怕你笑话我是多么地渴望能够再次地见到这位美丽的姑娘,每次我出差列车经过吉林附近的那家小站我都扫上几眼,希望她再次地出现。然而,每次的希望都变成了失望。
时间过的真快,我由青年过度到四十多岁的中年,我想那位曾经邂逅的姑娘应该也是我这个年龄了,她还是那样漂亮?我心里仍然留有侥幸相逢的莫名渴望。
一九九五年深秋的一天,当火车在吉林附近的那家小站停靠时,车上一下子上来了很多的人。人丛中有个女人特别觉得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但又觉得有些陌生。
“妈妈,这里有个座位,您就坐这儿吧。”一个年轻的姑娘挎着包裹迅速地挤了过来,中年女人在她女儿的帮助下坐在我的身边。
零距离的接触,我发现这位叫着妈妈的姑娘和我二十多年前曾经相识身着天蓝色汗褂的美女长相一模一样。莫非她是……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我眼前的这位姑娘和二十多年前的那位姑娘是十分地相像,但是理智清晰地告诉我她绝不是从前的伊人,或许她的妈妈是。
“先生,你也去哈尔滨呀?”中年女人说话了。
“是的,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怎么就觉得眼熟。”我应承着。
“我也觉得眼熟。哦,想起来了,也在这里,我们也是坐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了。”
是她,一点没错,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期盼着那个身着天蓝色汗褂貌美的姑娘。
可是,朱颜已改,青山不在依旧,我身旁的中年女人容颜苍老、相貌平平,昔日国色天香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我从热切的无数个期盼中一下变得失望起来。
懊悔极了,我不希望看到是眼前的真实,只想保留一个完美如初的虚幻——我一直期盼着的那个身着天蓝色汗褂的貌美姑娘,让那份美好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魅力四射,绵绵不绝。
冷峻说什么是艺术?被遮住的那一部分可望不可求的想象张力就是艺术。否则,就像业已存在的事实一旦暴露无遗许或真相大白,它所折射的魅力便走向了死亡的境地。